
吸管妞导语
初冬正是义乌红糖飘香季,红糖作为义乌著名特产,承载着义乌“鸡毛换糖”的厚重历史。从明末清初开始,义乌人就开始走街串巷,用“鸡毛换糖”换取蝇头小利,这也是义乌人最早的经商启蒙。“鸡毛换糖”精神激励着义乌几代人,也推动着义乌成为世界闻名的小商品城。
对此,吸管妞将结合“双童”楼仲平口述的“鸡毛换糖”经历持续推出《末代货郎楼仲平“鸡毛换糖”回忆录》系列!今天和大家分享系列第一篇:


“鸡毛换糖”发源地位于义乌东部的廿三里街道,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明末清初。以当时的红糖加工业为基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鸡毛换糖”大约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历史。义乌的拨浪鼓声响遍了周边省市,“拨浪鼓之乡”也由此得名。

我14岁从“鸡毛换糖”出发,从事过二十多个行当,几次起死回生,历经坎坷。回头想想,我的“鸡毛换糖”之路也挺精彩。趁义乌红糖季期间,我也和大家讲讲我的“鸡毛换糖”故事:

我出生于1965年,正经历了动荡十年,家中有兄妹六个,我排行三兄弟最小,下有两个妹妹,上有奶奶和父母,一家九口。
在我出生之前,我的父母带着我的大哥二哥和姐姐穿行于江西与义乌之间,背着村里在江西偷偷地搞资本主义尾巴的“鸡毛换糖”,原因是我奶奶和叔叔在那边,所以当时我们一家子会阶段性地到江西上饶地区,偷偷在当地开荒种一点粮食。所以我每次遇到江西老表都会说我也是半个江西人。

六十年代末期的动荡灾难正处于水深火热中,地贫加上人祸导致义乌地区在六七十年代处于极端贫困当中,我从小有记忆开始就是饿,极端的饿,对吃大米饭有一种强烈的渴望。

那个时候的我好像除了找吃的还是找吃的,到处找野果,满地捡柴火,到邻乡捡菜叶,到隔壁乡捡稻穗头,沿着铁路线捡煤渣。大雪天还拿着锄头在大哥二哥带领下到农场麦地里挖遗留的番薯根……
我记忆中的第一次出远门就是跟着父亲和奶奶从江西弋阳城里连续跑了百把里地到达弋阳北部的漆工镇。我父亲挑了个货郎担,妈妈在家里没有过来,我和奶奶一路跟着父亲的货郎担走,一天走到晚,就是为了能吃上一顿白米饭。

“鸡毛换糖”的季节通常都在每年春节前后的一个月,这也是我们几个小儿最害怕的时候,父亲通常会在腊月初就出去了,而这个时候也是农村最青黄不接的时候,到五六岁的时候我们一家已经有九口之人,生产队工分仅靠父母两个去赚,由于吃的人多,赚的人少,每年反正都会缺粮(当时我们属于缺粮户,要交一定数量的钱后才能根据户口配置粮食供应),交给生产队的缺粮款全靠“鸡毛换糖”解决。

我的祖先从明清开始就有在春节期间外出“鸡毛换糖”的传统,但在动荡时期,“鸡毛换糖”是投机倒把,绝不允许有人私自公开以做生意的由头从事这个营生,一直到1970年后才逐渐集体审批拿着介绍信,以收集鸡毛做肥料的理由进行“鸡毛换糖”,虽然有一个合理的借口做挡牌,还是会时不时被江西方面抓起来挨打游斗并拘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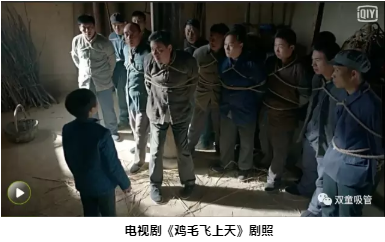
儿时记忆最高兴的是两件事情,一是每次父亲出去“鸡毛换糖”。要回来的那天我就一大早到大路口去等父亲回来。二是每年的春节能有粽子和大米饭吃。春节对于每个小儿梦想自不必说,而我父亲回来肯定也会买或带一点奶奶那边的“回头货”,每次基本是正月初十左右的傍晚时分就去村路口等了,从弋阳回来的火车是下午到义乌的,大老远看到一个挑着担子的人都会远远地跑过去看是不是我爸爸。

父亲在春节后”鸡毛换糖”回家,也通常会挑着大包小包的山货,这些山货通常是鸡菌皮(一种杀鸡时从鸡胃里面剥出来的黄色中药)、甲鱼壳、牙膏壳、女人长头发和破凉鞋等,这些所谓的山货比较值钱,往往可以偷偷地拿去换一点钱补贴家用。

“鸡毛换糖”换来的鸡毛由于数量较多要等到火车托运回来后交给生产队记工分(以前农村考核社员的一种计分)而充当副业费。父亲回来后我会整天跟着他到农村市口去换山货,每次换山货后等待的就是爸爸肯定会买一个只有这个时候才能吃到的麻饼。三兄弟中我最小,我一直以来感觉爸爸也最疼我,这是我记忆中最最幸福的事情。
